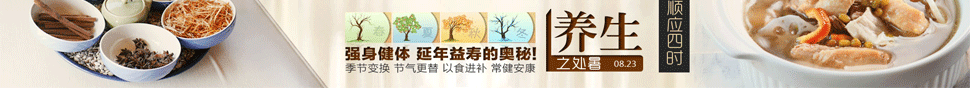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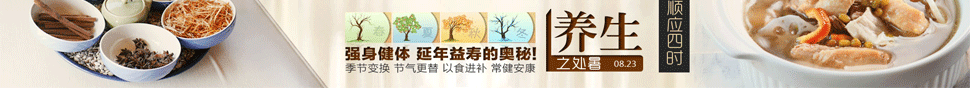
一
年1月,在延安,我从中央研究院调到了解放日报社。这是我做新闻工作的开始。
解放日报社在延安有名的清凉山上。清凉山靠近延安城,在城的东北角,中间隔着延河,它就在延河之滨。在这座山头上还有新华社。我一到清凉山,就听说新华社每天除了发文字广播,还有口头广播,口头广播的电台叫做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延安台是在年底建成的。当时延安遭到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物质条件极端困难。发射台的发射电力只有二百多瓦,发动机是用一个旧汽车头改装的,燃料是木炭,因此电压很不稳定,广播出去的声音忽高忽低,常常听不清楚。我到清凉山不久,就听说因为播出效果不好,一时又很难改进,加上发射机发生故障,只好停播了。
年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延安军民万众欢腾。这天晚上,我们正在紧张地工作,忽听得远处一片锣鼓和鞭炮声,从清凉山上向城南新市场一带眺望,高举火炬游行的人们,象是几条火龙在飞舞。听采访回来的同志说,有些人是把自己的破旧棉衣浸上油当火把的,还有些商贩把零售的小食品分送给游行的人们。延安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
新华社的同志把唯一的一台收音机安上广播喇叭,摆在窗台上。很多人都跑到窗前的山坡上听广播。这天晚上,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改变了日常的广播节目,反反复复地广播以蒋中正名义发表的所谓“命令”,“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就地待命”,而叫伪军去受降并维持治安。抗战八年,蒋介石躲在峨嵋山上,现在要下山来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了。大家听了非常气愤。
我跑去找博古同志。他当时是解放日报社社长,又是新华社社长。我到了他住的窑洞里,他正在给军委三局局长王挣同志打电话。等他放下话筒,我告诉他刚才听到的广播。他说,党中央已经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正在准备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又说,在这个时候,急需把我们自己的口头广播恢复起来。原来那部发生故障的发射机早已修好了,已经用于文字广播。王挣同志答应再作进一步的改装,很快就可以恢复口头广播。我听了很兴奋。
就在这天晚上,王挣同志召集三局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开会,作了紧急动员,布置突击改装发射机的战斗任务。十几位同志连续奋战了几昼夜,终于胜利地完成任务。试播的那天晚上,我们又聚集在山坡上收听。虽然因为电波越距未能听到,但是从敌后各根据地和从重庆等地发来的电报,知道他们听到的声音是清楚的。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9月5日正式恢复广播。这一天,是延安军民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的日子。广播报道了庆祝大会的消息,宣传了全国军民,特别是各抗日根据地军民艰苦抗战八年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表达了延安及各根据地军民为保卫胜利果实和建立新中国而继续奋斗的坚定立场和坚强决心。`我国人民广播史上的一场新的斗争就这样开始了。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广播的时候,我仍在解放日报社工作,主编副刊。我们非常重视延安台。《解放日报》及时报道了延安台恢复广播的消息,副刊连续发表了几篇介绍延安台的文章,还陆续选登过延安台播出的几十篇专稿。
二
年6月,延安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进行了大改组。这是当时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抗战期间,党中央直接掌握着两个新闻宣传工具,一个是延安《解放日报》,一个是新华社广播(包括文字广播和口头广播)。在长时间内,对这两个新闻宣传工具,是以《解放日报》为主,重要的消息、文告、社论和文章等,都是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然后新华社选择和摘编报纸上的东西,进行广播。年6月,到了全面内战爆发的前夜。这种新的形势要求把重要的消息、文告、社论和文章等,及时地先由新华社播发,同时发给《解放日报》。因此,新华社的机构需要扩大,而解放日报社的机构可以相应缩小。当时,新华社成立了几个编辑部,其中之一就是语言广播部,我们习惯地叫它口头广播部,也就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编辑部。新华社最早只有一个口头广播稿的编辑,以后逐渐增加到五个同志,成立了语言广播组,由杨述同志担任组长,编辑有张纪明、韦君宜、苗力沉、刘志云同志。改组以后,人员有了变动,杨述同志调任新华社秘书,张纪明同志调到新华社解放区部,另外又调来刘衡和高虹同志。我调到语言广播部任主任,开始兼《解放日报》副刊部的工作,后来杨思仲(陈涌)同志接替了我在副刊部的职务,我才专门做口头广播工作。
延安《解放日报》编辑部原来占用在半山腰的两排十几孔石窑洞,改组后新华社几个编辑部也都搬到这里办公。由于窑洞比较少,语言广播部就和副刊部挤在一个窑洞里。
随着新华社的改组,原来由军委三局管理的广播电台的发射台和播音室、机务人员和播音人员,也划归新华社统一管理。新华社成立了电务处,统一管理文字和口头广播的机务工作。因为播音室跟机房在一起,播音员都列入了电务处的编制,但业务上播音工作由编辑部领导。原来播音室在西北郊裴庄,发射台在阎店子,离清凉山有三十里左右,这时都搬到离清凉山不到五里路的文化沟,以后又搬到更近一些的北关。当时美军观察组住在北关,用电的条件比较好。
延安台在年到年播音期间,最早的播音员是姚雯同志,以后是徐瑞章同志,肖岩同志。年重新恢复广播的时候,开始是慕琳同志,以后调来了孟启予、于一同志。到年春天,又调来了钱家相同志,机务组有毛动之(组长)、刘振中、刘致远、李志海、武荣华等同志,他们都是既负责文字发报,又负责口头广播的机务工作。
三
语言广播部成立的时候,草拟了一个暂行工作细则。细则规定语言广播部的任务是:“建设全国性的语言广播机关,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报道国内外时局的动向,有计划与有系统地宣扬我党我军与解放区的事业和功绩,揭发国民党的腐败黑暗统治并宣传与鼓励其统治区广大人民的民主运动。”这里说的“建设全国性的语言广播机关”,就是说要办成面向全国的广播电台。它以全国人民为宣传对象,但重点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听众。根据这个任务,细则对节目的组成、稿件的编写、工作的程序、人员的分工、业务的研究等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开头,延安台每天播音两小时,分两次:一次在中午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半,一次在下午六点到七点。节`目有:新闻、通讯、评论、解放区介绍、解放区政策讲话、故事、记录新闻。在全面内战爆发后,每次播音增加了半小时的《对国民党军广播》节目。从年9月5日起,也就是从延安台恢复播音一周年的日子起,把下午播音时间又延长了半小时,增加了广播评论、演讲、人民呼声等节目。
新闻、通讯、评论节目的广播稿,都是根据新华社发的文字电讯稿,按照国民党统治区听众的需要进行选择,按照口头广播的特点和要求进行加工、改写而成的。广播评论、解放区介绍、解放区政策讲话这几个节目的广播稿,都是我们自己编写和组织的。广播评论主要是对国民党统治区发生的一些事件发表的评论,有些事件,新华社不发表评论,延安台有需要,我们就自己写。解放区介绍节目,系统地介绍了当时十九个解放区创建的历史和现状。解放区政策讲话节目,讲解了解放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所实行的政策,有些是跟国民党统治区对比起来讲的。请知名人士演讲,当时没有录音设备,都是请到播音室里直接播讲。朱德、林伯渠、王震、廖承志等同志都播讲过。因为交通不便,请人播讲很不容易,所以讲演的次数不多。遇到特别事件,有时候还办特别节目,例如,为了配合国统治区人民举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延安台曾经举办连续十天的特别节目,请知名人士作广播讲话,揭露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独裁卖国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把美军赶出中国。在人民呼声节目里播出的,都是从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报刊上选的爱国民主人士和各阶层人民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文章和公开信,仅年7、8两个月,就广播了三十四篇。针对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现状,延安台除去报道了解放区物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新闻和通讯外,还办过《行情》节目,报道解放区一些新解放城市的物价,跟国民党统治区物价作对比。
对国民党军广播节目,曾经起过特殊作用。它的内容,除去向国民党军队宣传战争的形势,讲解我军的政策,给他们指明出路以外,大部分时间是播送起义和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军官名单,包括姓名、年龄、职别、籍贯、起义或放下武器的地点、家属通讯地址等。还报道他们到解放区以后的生活情况,广播他们写给家属、亲友或同事的书信。
延安台的广播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影响。我们曾经接到过从北平、南京、昆明、重庆等地突破重重封锁带到延安的信。听众在信里热情地告诉我们,他们怎样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地收听延安广播。有个学生说,他常常是关起宿舍的门,躲在被窝里收听。有一封信里说:“听到延安的声音,就象在茫茫的黑夜里见到了光明。”国民党军的军官也有很多人十分注意收听延安广播,许多起义和放下武器的军官都说过,他们是听了延安的广播,明白了内战的起因、形势和前途,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策,才下决心走到人民方面来的。年6月26日,原国民党空军_L尉刘善本驾机起义,飞到延安。他告诉我们,他就是收听了几个月延安台的广播,看清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在6月17日又听了延安权威人士关于反对美国国务院提出军事援蒋法案的声明以后,下决心离开内战的漩涡,投奔延安的。我们请刘善本向国民党空军人员作了两次广播讲话,一次的题目是《赶快退出内战漩涡》,另一次题目是《谁是谁非—谁是燃起内战烽火的罪人?》。后来有二十几位国民党空军陆续起义,他们都说是听了刘善本的广播讲话,才下决心到解放区来的。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进步报纸,经常抄收延安台的记录新闻,改头换面地刊登在报纸上。海外侨胞办的《华侨导报》、《怡保日报》等,也经常抄收刊登延安台广播的消息。
当时延安台的发射电力比较小,但是由于有电力较强的张家口、邯郸和齐齐哈尔等地的新华广播电台转播,因此,延安台的声音传播得比较远,香港、南洋一带也都能收听到。
四
在延安,我们的生活是紧张的,艰苦的。
前面说过,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编辑部离播音室有几十里路,为了赶上播音,每天必须在下午两点钟以前把稿子编好,交通信员骑马送走,遇到急稿,我们往往顾不上吃饭,几个人同时编的编,抄的抄,才能不误发稿时间。有时候连这样做也来不及,只好用电话将稿子传给播音员,她们记录下来再广播。在延安,电话传的声音有时很微弱,打电话是很困难的。
送稿要过延河。遇到夏季山洪暴发,河水猛涨,通信员就把稿子用油布包好,顶在头上,泅水过河。在洪水中游泳是很危险的。有一次,我走到延河边,刚要过河回清凉山,看到山洪奔腾而下,我想抢在浪头到来之前过河,不料走到河中间,浪头已冲到身边,冲得我直摇晃,幸亏有位老乡推着我才游上了岸。上岸后,我浑身都是泥浆,除了两个眼珠外,满头满脸都糊上了一层泥浆。回到清凉山,泥浆被太阳晒干了,我变成了一个泥人!
那时候,没有录音设备,播音员都是直播。在正常情况下,要让播音员有一段准备时间,如果稿子送迟了,播音员就没有多少时间准备,有时候,甚至根本来不及看一遍稿子,就该播音了。
组织文艺节目,更不容易。平常的文艺节目都是播放唱片。当时有二十多张唱片,其中多半是京剧,也有世界名曲,新歌曲的唱片很少,只有《渔光曲》等几张。因为唱片太少,只好反复使用。有时,播音员唱几支歌,说几段快板,也作为一次文艺节目。电台的工作人员中,有几位会拉会唱的,有时也组织一次文艺节目。有几次,我们还请军委总政文工团和鲁艺的同志到电台演播文艺节目。他们住地离电台远,我们都是向部队借用卡车接送。文工团的人比较多,窑洞里站不下,就站在窑洞前的山坡上演出,有时候山坡上的羊叫声,也会混着播出去了。
我们住的是窑洞,冬暖夏凉,还算舒适。吃的主食是小米,有时吃馒头或面条。菜一般是煮白菜、萝卜、南瓜等,有时还有点肉,都是用大木桶打到办公室门口,每人用瓦钵子分了吃。我们写稿用的纸是有光纸,写信多半是边区自己用马兰草造的纸,信封都是用旧报纸糊的,而且往往是正面用一次,背面用一次,然后贴层白纸,再用一两次。
年,陕甘宁边区发生了旱灾。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开展了生产救灾运动。社里成立了救灾委员会,把全社人员,包括家属,除老弱病残和十五岁以下的儿童外,都组织起来,编成一支劳动大军。抽出二十五人组成一支突击队,到南劳山农场抢种五百亩秋田,定的任务是生产细粮五十石。其他人员利用附近荒山地,大量种小日月糜子、荞麦和南瓜、洋芋、萝卜等,再加上挖野菜等办法,每人要完成能折合一斗粮的任务。同时,厉行节约。为了节约粮食,每人每天定量为十四两(折合现在十两制为八两多),并且严格执行按人下米做饭,不够就用瓜菜代替。原来规定每两年发一套棉衣,每年发一套单衣,也停发了。过冬,大家就组织起来,集体互助,把旧棉衣拆洗缝补了再穿。没有换洗的衣服,就到山沟里的小河边,把衣服脱下来洗干净晾好,然后到河里洗个澡,等衣服干了再穿上。年第四季度,连日常经费和个人津贴也停发了。全社人员又组织起来,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实现了缝补用布、添补棉花(添补旧棉衣、棉被用的棉花)、棉鞋、蔬菜、木炭、马草等完全自给,连一部分办公用品,也要用自己生产得来的钱买。过去还发灯捻,后来不发了,点完了就把棉被里的棉花扯一块搓成灯捻点灯。破得不能再穿的衣服,就撕成布条打草鞋。工作和生活条件这样艰苦,可是同志们为了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都以苦为乐,以艰苦奋斗为荣。
五
年6月底,全面内战爆发,蒋介石对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各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仅仅四个月的时间,就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计划,使其兵力遭到重大损失。此后,蒋介石不得不把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个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为了对付和粉碎蒋介石对陕北的进攻,11月11日,党中央召开了中央机关和延安地区一千多人参加的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动员大会,彭德怀副总司令、朱德总司令、刘少奇同志等先后在会上讲了话。彭德怀副总司令号召全体干部要准备过更艰苦、更紧张的战时生活,准备多少人住一间窑,准备拿大腿做办公桌,准备随时随地无条件地服从命令,全心全力去争取胜利。朱德总司令在讲话中号召边区三十万壮年男子和三十万壮年妇女,都紧急动员起来参加战争,人人学会最简单的埋地雷和投手榴弹两项战术,实现全民皆兵,来保卫边区。刘少奇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必须按战争的需要,改变全党的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11月12日,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又召开了边区一级干部的动员大会。这样,全延安和全边区党政军民立即进入了备战状态。12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关中,延安和边区又从备战动员转入战斗动员。
在备战动员和战斗动员之后,新华社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分批疏散到延安东北一百八十里的瓦窑堡,只留下少数人坚持工作。语言广播部留下来苗力沉、刘志云、杨兆麟和我,杨兆麟同志是从南京撤退到延安的,分配到语言广播部工作。播音员留下来钱家相同志,她坚持到最后撤离延安。临时调来播音的有杨慧琳和吴作贤同志,但这两位同志播了没有多久也疏散了。
语言广播部原来在清凉山西边山头的石窑洞里办公。备战以后,搬到了东边山头的一孔土窑洞里,这孔窑洞里有防空洞。由于人力减少了,一个人得做两三个人的工作。为了防御敌机轰炸,播音室和发射台又从文化沟搬回阎店子。这又增加了我们工作的困难和紧张。
我们在紧张的工作中,每天都要进行军事训练。当时我们都编成了自卫军,每人发了枪支和子弹,要求大家在和敌人遭遇时,能够消灭敌人,保护自己,在发现敌人伞兵时,能把他就地消灭。大家都怀着对敌人的仇恨和必胜的信心,认真进行操练和打靶。第一次打靶时,每人打了三枪,一般的都打了十几环,有的打了二十几环,成绩还不错。每天夜晚,我们还要轮流站岗放哨。大家都没有手表,就用点香的办法计算时间,点完两支香,换一班岗。我们一边工作,一边准备战斗。当时清凉山上的医务人员也都疏散了,他们留给我一个药箱,里面有一些常用药品,还有绷带、药棉等。因为我有一点医药知识,临时又成了医生。
六
年3月13日中午,我们得到通知说,蒋介石、胡宗南军队即将向延安发动进攻,要准备好派人到瓦窑堡安排文字广播和口头广播的接替工作。等到下午四点多钟,接到命令,要我们立刻到瓦窑堡去。范长江同志和我乘吉普车连夜赶赴瓦窑堡。在漆黑的夜色里,路很不好走,吉普车整整跑了一夜,天蒙蒙亮的时候才到瓦窑堡。我们向廖承志同志报告了战争发展的情况和接替工作的任务。廖承志同志紧急作了具体的安排,从原来疏散到瓦窑堡的人员中留下十多人跟我们一起做接替工作,其余的人员由他和其他同志率领,立即向晋察冀进发。他们准备到那里去建立新华社和陕北台。留下的同志由范长江同志负责,马上组成了一个临时编辑部。这个编辑部统一担负文字广播、口头广播和英文广播以及翻译、译电的全部工作。口头广播稿的编辑只有我和张潮同志两个人,他原来是《解放日报》的记者。我们十几个人集中在一个大窑洞里,搭起门板当桌子,垒起土坯当凳子。范长江同志坐在靠墙的土炕上审稿。我找了一块木板垫在大腿上,坐在土坯上编稿子,每天还是要编八千多字,上午编新闻性的节目,下午编第二天要播出的《对国民党军广播》的稿子,主要是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的军官名单和他们的书信。
延安台撤离延安前的最后一次播音是3月14日中午,是在敌机狂轰滥炸下播出的。当天晚上,我们就在瓦窑堡接替播音。当时的播音员是杨慧琳和夏沙同志。瓦窑堡开始播音以后,在延安的工作人员17日全部撤退,19日到瓦窑堡。钱家相同志留下播音,夏沙同志去晋察冀。
瓦窑堡的播音室和发射台在好平沟,离编辑部所在地史家畔二十五里路。通信员常常另有紧急任务,广播稿编好后,就由编辑送到播音员那里。这时候的播音室非常简陋。一座破旧的小土地庙,有两层,上层做了播音室和播音员宿舍,下层是机房和机务员宿舍。播音室只有四平方米左右,话筒放在一张只有三条腿的桌子上。门上和室内挂上羊毛毡,用来隔音。在3月19日我军主动撤出延安以前,我们还是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从20日起,改名“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为了防御敌机侦察轰炸,停止了中午的播音,只在晚上播音。
3月25日傍晚,我编完了稿子去广播电台。走到村口的时候,看到了周恩来同志的背影,有个警卫员跟着他。后来听说周恩来同志是来向军委三局王挣等几位领导同志布置撤离瓦窑堡工作的。他指示在撤离的时候,保证新华社文字广播和口头广播不要中断。我走到播音室下面,朱德同志来了。他问:“现在播音吗?”我说:“正在播音。”他要我陪他到播音室去看看。我们轻轻地走进播音室,钱家相同志正在播出最后一个节目。朱德同志等她播完,跟她亲切地握手。朱德同志告诉我们,我军在青化砭打了个大胜仗,正在清查战果,查清了就要发战报。他说,他今天就要离开瓦窑堡了,要我们在播出这个消息后,再从瓦窑堡撤走。这个消息我们是在三天以后,3月28日晚上播出的。
3月28日中午接到中央的命令,要我们当天晚上撤离瓦窑堡。我们是中央机关中最后撤退的一个单位。当天晚上,播音员播完了全部节目,又跟机务员一起把机器埋藏好,从好平沟急行军赶到史家畔。编辑部的同志们也已经搞好坚壁清野,把不能带走的稿子都烧毁了。这时已是深夜12点多钟,一支三十多人的队伍,在范长江、刘祖春和我三个人组成的队部的带领下撤离瓦窑堡。天很黑,夜很静,我们按照军用地图标出的方位,并由一位熟悉山路的老乡带路,穿过山间羊肠小道,几乎不停地走了三十几个小时,到了绥德的田庄,才赶上中央纵队队部。
我们到达田庄,得知晋察冀不能接替新华社的工作,特别是没有机器设备接替陕北台的广播。中央已经决定由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临时新华总社,由邯郸新华广播粤台临时接替陕北台,并要我赶到邯郸去。当即指定由我负责组成一个小队,其中有播音员钱家相同志,还有文字广播的王宗一、何力夫等六位同志。我们在3月31日下午出发,到宋家川乘小帆船,依依不舍地离别了陕北,渡河东去。
七
我们东渡黄河,到达晋西北,沿着在乡间小镇设立的兵站,一站一站地前进。我们每天走一站。站和站之间的距离大多是六十里左右,最短的是三十里,最长的有一百二十多里。我们走的都是山上的小路。在洪洞县和赵城之间有敌人设置的一条封锁线。在兵站的统一安排下,我们八个人和中央其他机关的二一十几个同志,其中有几个是带着小孩的女同志,由民兵护送,一起过封锁线。封锁线是约五里宽的开阔地,密布了地雷,沿线大约每隔五里路就构筑了一座碉堡。敌人日夜守在碉堡里,夜间用探照灯不断地来回搜寻。我们在过封锁线之前,作了认真准备,不能让小孩哭,不能让牲口叫,以免被碉堡里的敌人发现。民兵是很有经验的。我们在他们的指挥和护卫下,不到一个钟头,就顺利地通过了封锁线。我们到了一个村子里,民兵轻轻地敲开了几户老乡家的门。我们进去的那一家,只有一位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大娘,她把我们引进屋里,让我们坐在炕上、凳子上,还忙着为我们煮了一锅小米粥。刚吃完粥,天还没有亮,民兵就来催我们上路。这一夜的经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人民间的鱼水深情。
过了封锁线,路好走多了。我们经过了一些县城,有些兵站还派大车送我们。我们从过了黄河之后,跋山涉水,走了将近一个月,走过一千多里路,其中有许多是迂回曲折的崎岖陡峭的山路,最后终于到达了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武安县冶陶镇。
在冶陶镇休息了一天,我就和钱家相同志一起赶到陕北台的新址。这时候的陕北台,和邯郸新华广播电台在一起,在原属河南省、现属河北省涉县的沙河村。这是太行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临时新华总社设在西戍村,离沙河村五里路。当时陕北台所用的发射机,是从强迫降落的敌机上缴获的报话机,经晋冀鲁豫军区三局的王士光等同志连续奋战了几个昼夜改装成的。3月31日赶装成功,当晚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试播,效果良好。从4月1日起,正式接替了陕北台的广播。陕北台在搬出瓦窑堡后停播了两天。在这两天,国民党广播电台大肆造谣,说陕北台已经被炸毁了。可是,过了两天,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声音又在天空传播,使他们的谣言破产。更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陕北台用的发射机是国民党“送来”的,发射电力四百瓦,比原来的还增强了一百多瓦。
我们身在太行,心里常常思念着在陕北的党中央,想念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他们每天都通过留在陕北的新华社工作队,发来需要由新华社播发的重要消息,有时还发来评论和社论。社论过去都是由《解放日报》发表的,用新华社名义发表社论,是因为党中央的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在撤出延安后停刊了。毛泽东同志还常常收听陕北台的广播。5月中旬的一天,我们收到新华社工作队从陕北发来的电报,说毛泽东同志听了陕北台报道蟠龙大捷的节目之后,认为播得爱憎分明,很有力量,应予表扬。我们表了播出这个节目的钱家稠同志,陕北台和邯郸台全体同志也都从中受到鼓舞。
年7月,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开始了全面大反攻。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之后,一天上午九点多钟,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在滕代远同志陪同下,来到陕北台和邯郸台视察。我和邯郸台台长常振玉同志向他们汇报了工作。我们围坐在一张方桌旁,邓小平同志听了汇报之后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现在全面大反攻开始了,我们的部队已经过了黄河,我们很快也要过河去。部队过河后,看不到报纸,要得到消息,就靠听你们的广播了。希望你们广播的新闻和记录新闻,要注意适应部队的需要,我们在行军和作战中每天都将派人抄收。他还说,希望你们办个对部队广播的节目,我们这支野战军的战士差不多都是晋冀鲁豫的子弟兵,希望你们经常把家乡的好消息告诉他们。我们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以后,陕北台播出新闻和记录新闻都注意了适应前方部队的需要。邯郸台开办了对在前线的部队广播节目,播出了许多子弟兵家属写的书信。过了不久,在前线的新华总分社发回电报说,过河的部队每天都抄收陕北台的记录新闻,并且把它油印出来发给战士,发给民兵。全军印发的这种油印小报的总数,最多的时候是一天六十万份。
7月上旬,从陕北转移到晋察冀的新华社同志,也全部到达太行。廖承志等领导同志来到后,立即恢复了新华总社。为适应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新华总社充实加强了各个编辑部。同时,在前线各部队中建立和扩大了总分社、分社和支社,组成了强大的前线记者网。口头广播部的编辑和播音员也增加了。从这时起,陕北台有了第一个男播音员,这就是齐越同志。前线总分社除向总社发稿外,还专门供给陕北台对国民党军广播需用的稿件和材料。陕北台的广播宣传得到了加强,播音时间,从年9月5日,即延安台恢复播音两周年起,每天增加到三个小时,以后又增加了每天半小时的英语广播。
全面大反攻开始以后,陕北台广播宣传的中心任务,就是为全面大反攻服务。年10月10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和《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八项基本政策。同一天,党中央还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和《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宣布彻底废除我国几千年来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陕北台大张旗鼓地连续十几天反复广播了这几个重要的历史性文件。年12月底到年1月初,又反复广播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杨家沟会议上作的重要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是我们党在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这一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上海、杭州、重庆等地,都有党的地下组织和进步人士秘密抄收陕北台广播的这些重要文件,并且油印散发。如中共重庆市委办的地下刊物《挺进报》,就曾经刊登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陕北台在广播这些文件的同时,还组织了大量的节目,对文件中提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
陕北台从广播《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那一天起,加强了对蒋军的政治攻势和分化瓦解工作。对于宣言中提出的对蒋方人员区别对待的方针,以及对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一律不杀不辱、愿留者收容、愿去者遣送等项政策,我们在广播中结合大量的具体事例,进行了反复的、有说服力的宣传。陕北台在这个时期播出了更多的报道起义和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在解放区生活情况的通讯特写,以及他们写给家属、亲友或同事的书信。这个时期,起义和放下武器的蒋军军官增多,我们广播的名单只能限于将一级的。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组织把这些名单抄下来,按照广播的地址写信给其家属。陕北台曾宣传他们可以经过联系后来解放区探望,例如王耀武的家属就派人来山东解放区探望过。
陕北台在这个时期对于新解放的城市作了大量的报道,及时宣传了我党我军在这些城市依靠人民群众肃清反动势力、建立人民政权、.实行民主制度、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及保护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救济灾民贫民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陕北台还报道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解放区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以及广大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热烈支援前线和努力发展生产的动人情景。广播通过这些宣传报道,教育、号召和动员待解放城市的人民,配合人民解放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人民解放军的大反攻势如破竹,国民党反动派日暮途穷,它妄图以新的和谈骗局苟延残喘,同时实行大搜捕和大屠杀,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进行更加疯狂的镇压。陕北台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和罪行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受到鼓舞,把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斗争不断推向高潮。上海工人的反迫害斗争,全国学生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全国人民反对美帝扶植日本运动,一浪高过一浪。陕北台对这些都作了充分的报道,并给以有力的声援。
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我们党进行了一次“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整党运动。年12月以后的几个月,陕北台开展了这个运动。这次运动对于教育革命知识分子,特别是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或者同他们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在土地改革中如何站稳党的立场、无产阶级的立场,有着重大的意义。陕北台的同志在运动中认识到,如果不能坚定地站稳党的立场,无产阶级的立场,思想和作风不纯,就不能正确地执行和贯彻党的政策。经过这次整党运动,大家在政治上、思想上都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陕北台的宣传,在这个时期的影响是很大的。它在宣传全面大反攻以后党的方针政策方面,在鼓舞、引导、组织和推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方面,在瓦解国民党军队和唤起其中一些军官下决心放下武器等方面,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八
在我们撤出延安一年一个月零三天,我西北野战军收复了革命圣地延安。这是我军在大反攻中取得的一个伟大胜利。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在胜利的形势下,离开陕北,于年5月到达河北省石家庄附近的西柏坡村(原属建屏县,今属平山县),和先期到达的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同志会合。西柏坡成为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新的所在地。新华社也奉命由太行转移到西柏坡附近。5月22日,陕北台在沙河村广播了最后一次节目,第二天就由在西柏坡附近已经准备好了的电台接替工作。
战争的胜利形势发展很快,全党面临着夺胜全国政权的伟大历史任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到了西柏坡后不久,党中央就决定,为了迎接全国胜利,全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各项工作的干部。8、9月间,党中央开始直接在政治上和业务上训练新华社的干部。范长江、陈克寒、梅益、石西民、吴冷西、朱穆之等二十多位同志集中住到西柏坡,在胡乔木同志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小编辑部,编写和处理重要稿件。大部分同志仍留在离西柏坡不到五里路的陈家峪,做日常的编发稿工作。
我留在陈家峪,负责陕北台的编发稿件工作。从这个时候起,新华社每天的电讯稿和陕北台每天的广播稿,全部都用铅字排出来,印出清样,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审阅。他们批改过很多稿件,对怎样掌握党的政策,怎样写好新闻和评论,怎样纠正文字上的缺点,提高写作能力和词章修养,都作过不少重要的指示。毛泽东同志还为新华社和陕北台写过不少重要的社论、评论和新闻。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由于有中央领导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悉心指导,我们边工作边学习,收获之多,提高之快,是空前的。
为适应全国胜利即将到来的新形势,经党中央批准,新华社进一步调整了机构,加强了对总分社和分社的业务领导,同时成立了广播管理部,除管理口头广播部,还负责统一指导分解放区各地广播电台的业务。这时在东北有齐齐哈尔、佳木斯屯哈尔滨、安东、牡丹江、延吉、临江等新华广播电台,`在华东有华东和济南新华广播电台。它们都转播陕北台的节目。晋察冀台(原张家口台)和邯郸台先后停播,大部分编播人员调到陕北台。
这个时期,口头广播部和新华社其他编辑部,先后设在平山县的陈家峪、韩家峪、通江口,离西柏坡都比较近。陕北台的发射台和播音室,开始的时候设在平山县的张胡庄,以后在井胫县天户村建造了一个较大的发射台,播音室又搬到天户村附近的窟窿峰。从太行转移到张胡庄的时候,陕北台使用的发射机是用从蒋军手里缴获的美制报话机改装的。在天户村使用的发射机是解放石家庄时接管的日本造的发射机。经过军委三局同志的改装,把发射电力由四、五百瓦提高到三千瓦。为了安全,发射机安装在地下窑洞。架设的天线,除了用木杆,还建造了两座高大的铁塔。这些条件,都比在延安时好得多。
工作比在延安更加紧张,更加艰苦。编辑部和播音室之间相距很远,播音室在张胡庄的时候,相隔三十多里,搬到窟窿峰以后,相隔八十里左右。为了安全,为了选择有利于发射的地形,发射台和播音室不得不设在这么远的地方。从编辑部到窟窿峰,中间隔着波涛滚滚的沱河,还有高山和丘陵。为了赶在每天下午把广播稿送到播音员那里,我们不得不通宵编写稿子,在黎明之前把稿子交给通讯员,骑马送走。遇到涨大水,淖沱河涨水有时比延河山洪暴发还要厉害,通信员就把稿子包好后装在竹筒里,泅水过河。有一次,浪高水急,通信员游不过去,是一位善于游泳的编辑把稿子送去的。有时候,没有人能过河,就把重要的消息用电话传给播音员,其余只好播旧稿子。口头广播部的同志们日日夜夜紧张地工作,在三大战役期间,不少同志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根本谈不上按时上下班,更没有什么休息日。
尽管这样紧张,工作秩序还是有条不紊的。口头广播部每天都开一次全体编辑人员的编前碰头会,一时间一般不超过十五分钟,内容是传达头一天审稿发现的问题和当天编稿应注意的事项。这个时期,我们还加强了调查研究工作,通过研究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研究国民党统治区的报刊,收听和研究国民党电台、美国之音等电台的广播,了解敌友我三方面的状况,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斗争、生活和思想状况,蒋军的官兵及其党政人员的政治和心理状况,使我们的广播宣传作到有的放矢。我们编写每一篇广播稿,都不仅注意政策性和思想性,而且注意针对性,还十分注意口头广播的特点和要求。廖承志同志审稿,除去审阅,还要审听。我们把稿子念给他和几个文化水平高低不等的同志听,等把不易听懂、念不顺口的地方都改好了,他才签发。播音员播前准备,播时监听,播后检查的制度也非常严格。认真掌握政策,加强调查研究,提高稿件质量,健全工作制度,高度负责,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这些都是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进行训练时提出的要求。
陕北台在这个时期的广播,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更大了。在一些待解放的城市里,有些工厂企业的工人,学校的学生,机关的职员,从收听广播中懂得了解放军的政策,纷纷起来保护工厂、学校、机关、仓库和建筑物等等,维持秩序,帮助解放城市和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在淮海战役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一个战役即将结束时,我军打进敌军的司令部,有个文书正在抄收陕北台的广播。问他干什么?他说,抄收陕北台的战绩公报,好向上级报告解放军俘获了我们多少人,有哪些军官投诚了,哪些军官被打死了,被缴获了多少坦克、大炮、枪支和弹药。这些我们弄不清,你们是查得很清楚的。后来了解到,蒋介石的总参谋部一也在抄收陕北台的广播。
九
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当天,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国民党的北平广播电台。随军进城的徐迈进、李伍、胡若木、杨兆麟、齐越等陕北台的同志进驻电台。从2月2日起,就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开始广播。
3月22日,得知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定于3月25日迁往北平,新华社、陕北台要派一批同志在此前一天赶到北平。在陈克寒同志带领下,我们分乘几辆军用卡车,日夜兼程向北平进发。24日凌晨,我们进了北平城,径直到了西长安街六部口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先到北平的同志和我们热烈握手拥抱。
3月25日下午5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同志来到北平,检阅部队。北平各界人士和群众代表举行欢迎式。我先赶到机场,采写了消息,用电话传到电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在当天下午五点钟的节目里,报道了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己经迁到北平的重要消息,同时宣布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已经跟随中央迁到北平,并从即日起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原来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以后改名“北平人民广播电台”,对本市广播。
从进城的时候起,陕北台就从新华社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6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管理全国的广播事业。第一任处长是廖承志同志。
北平台所用的技术设备全套是从国民党北平广播电台接管来的。这是一个破烂摊子。它有一部一百瓩的中波发射机,因年久失修,只用了其中十瓩的一小部分。架设天线的铁塔,也被拆掉变卖了。我们接管之后,经过清理,很快全部修复了发射设备。
北平台的广播节目和广播时间迅速增加。除普通话广播外,增加了对华侨广播的广州话、厦门话和潮州话等方言广播。外语广播除英语外,增加了日语。每天播音时间从七小时半增加到十二小时半。
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定都北平,并改名北京后,北平台改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10月1日,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开国大典的实`况。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北京台改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改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属于政务院新闻总署,管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全国广播事业。并且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把发展人民广播事业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从此,我国人民广播事业进人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七日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